摘要]在后殖民文学的语言问题上,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问题,从语言选择中判定民族忠诚的高低则是一种更为肤浅的看法。

不!我没有必要在白人面前哭诉我的仇恨 我也没有必要在白人面前喃喃我的感激
法兰兹·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
本文作者宋国诚,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在众多的非洲后殖民作家群之中,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原名詹姆士.恩古吉(James Ngugi),是一位最富民族独立意识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作家兼评论家。在一群誓言夺回被殖民者涂改扭变之“民族原形”,决心恢复非洲原住民在语言、宗教与文化之自我表述权的作家与艺术家当中,提安哥始终前后一贯、坚持到底。在有关非洲文学究竟应该回复母语写作还是继续使用英语写作的争论中,提安哥的观点始终居于论战的中心。他的“母语优先”立场,他对有关语言殖民、文化侵略、书写反抗的反思与探索,都已成为后殖民论争(post colonial debate)的焦点所在。提安哥1938年1月5日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Kamiriithu)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地理上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称为“白色高地”(White Highlands)的行政区域。提安哥隶属肯尼亚最大的氏族基库裕族(Gikuyu),父亲是个农夫。提安哥成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出生时家族的土地就已被殖民者强占取走,他的母亲因为哥哥参加反英游击队而遭监禁达三个月,他的叔叔因参加反殖民斗争而惨遭杀害,他的亲戚和长辈朋友也经常被冠上反英罪名,在家中遭到掳获而强行拖走。1952年,肯尼亚进入所谓“紧急状态”,所有本地学校被迫关闭,只有英语学校正常教学,提安哥于是从14岁开始学习英语。因教会学校强迫灌输英语教育使年轻的提安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后来在认清了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本质以后,他彻底拒绝了对基督教的所有信仰。对早熟的提安哥来说,童年的生活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边是“基库裕(Gikuyu)、非洲人(African)”,一边是“西方人(Westerner)、基督徒(Christian)”,这种背景决定了提安哥早期作品充满了“文化冲突”的题材,以及一种诉求文化抵抗的意志与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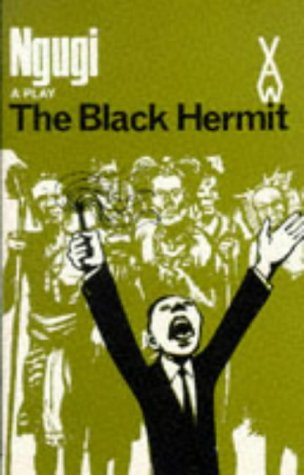
1962年提安哥在“非洲英语作家研讨会”上遇见了索因卡(Wole Soynka)和阿契贝(Chinua Achebe),这次重要的会面使提安哥决心走上“终生非洲作家”的道路,同年,提安哥创作了剧本《黑色隐士》(The Black Hermit)。1963年提安哥毕业于乌甘达的马基瑞里大学(UniversityofMarkerere)英语系,1964年再赴英国里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深造。在此期间,提安哥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兹.法农(FrantzFanon)思想的重大影响,也创作了他生平两部重要的后殖民小说《界河》(The River Between)和《一粒麦子》(A Grainof Wheat)。小说出版后,提安哥毅然改掉自己带有殖民象征的名字Jamesn Ngugi,恢复他基库裕族的本族姓名。作为提安哥第一部具实验性质的剧本《黑色隐士》,难能可贵地表达出提安哥对非洲部落主义的深刻反思。剧本描写了肯尼亚这一国家界于古老和现代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城乡矛盾,根据乡村部落习俗,家庭中的弟弟必须“再娶”哥哥死后的遗孀,而一场没有爱情的习俗婚姻不知造就了多少人伦悲剧。通过这一剧本,提安哥表达了部落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东非社会的三大毒瘤,若不拔除,东非人民将永远处于迷失和蒙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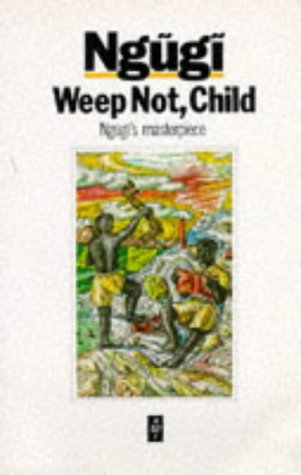
《孩子,别流泪》(Weep Not, Child)这部仅有136页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64年,写于提安哥在英国读书期间,也是东非作家在英国出版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故事采取“励志体”(Bildungsroman)形式,以1952--1956年“茅茅革命”(MauMau Rebellion)期间为背景,描写一位少年尼奥洛吉(Njoroge)成长的故事。少年原本成长于虽然贫困但也算平静无忧的家庭,他始终期望自己能够好好念书以光耀族门,实际上他也因自己的勤奋而成为部落中受尊敬的学者。然而,他的父兄为了反抗殖民地主的剥削,弃田罢耕,藏匿于森林之中,领导当地的游击队进行抗暴和暗杀行动。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尼奥洛吉深知个人美好的理想与愿望,即使内敛深藏于内心也不可久留,个人终究不敌外部世界殖民主义残酷的现实,即使他深爱地主之女,但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阶级对立下,终于把他推向反抗权贵和殖民统治者的战争。在这部小说中,提安哥试图探索真诚的爱情能否超越阶级对立与殖民冲突的可能性,但似乎这一美好愿望终究以失望告终。